立春刚过,墙角的迎春就迫不及待地绽出第一朵鹅黄。老花匠陈伯说这是"偷春",要折去头茬花枝才能开得整齐。可那些金黄的小喇叭哪管这些,只管在料峭的风里摇头晃脑,把春消息传得满街都是。
二月兰最是性急,还没等泥土化透就钻了出来。淡紫色的花瓣薄如蝉翼,偏要成片地开,远看像谁打翻了颜料罐。它们常挨着残雪生长,冷香里带着冰碴子的清气,城里人叫它"诸葛菜",乡下人却只当是喂猪的好饲料。
玉兰开花时最有声势。光秃秃的枝干上突然擎起千百盏瓷碗,白的似雪,紫的如霞。某年倒春寒,整树玉兰冻成了冰雕,陈伯连夜烧了炭盆围在树下。天亮时,那些冰壳包裹的花苞居然继续绽放,只是每片花瓣都凝着晶莹的冰脉,像是把寒冬也化进了自己的骨血里。
雨水节气前后,山桃野杏争相吐蕊。薄命的花瓣经不得风吹,一场夜雨就铺满青石板。清晨扫街的老王总留着它们不扫,说这是"香尘"。孩子们上学路过,踩着粉白的花毯,鞋底沾的尽是春天。
最耐人寻味的是牡丹园里那些老桩。看似枯死的枝干,某天清晨会突然鼓起暗红的芽苞,像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。陈伯说这是"花魂醒了",要备下腐熟的鱼肠肥。待谷雨前后,碗口大的花朵压弯枝头时,任谁都能闻见那藏了一整个寒冬的富贵气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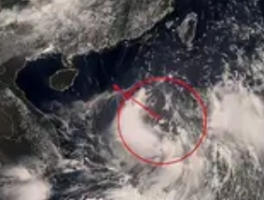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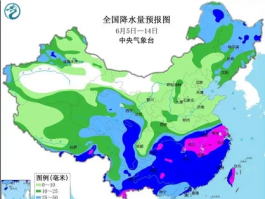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